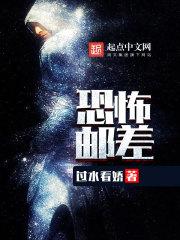鹅绒锁>娱乐:全网黑的我,被中科院连夜捞走 > 第152章 要通过现实找知识(第2页)
第152章 要通过现实找知识(第2页)
更可怕的是,他并非孤身一人——他的背后,站着整个华夏的科研体系。
一个正在以惊人速度崛起的科学强国。
鹰酱的科学家们意识到,楚衍不仅仅是一个科普主播,更是一个象征。
他的存在证明,华夏的科研生态已经培养出了一批既精通专业又擅长传播的复合型人才。
而这种能力,恰恰是西方学界最缺乏的。
他们或许仍能产出优质论文,但在科学传播,公众认知塑造方面,已经远远落后。
最令他们不安的是,楚衍的影响力正在迅速扩散。
他的直播吸引了数百万观众,其中不乏年轻的科研苗子。
如果他成功将华夏的科研精神,方法论乃至价值观传递给下一代。
那么未来十年,全球科学格局的天平可能会彻底倾斜。
他们面对的,或许是一个比任何技术封锁都更棘手的挑战。
一个能用通俗语言诠释宇宙奥秘的天才,正在东方点燃科学的火种。
中科院的院士们在观看直播时,立即启动了一项跨学科研究计划。
大家都开始探讨一个根本性问题,人类认知是否存在理论极限。
研究团队从三个维度展开论证。
一是大脑神经突触的可塑性边界。
二是信息存储的物理限制。
三是知识结构的自指困境。
但个体认知能力却受限于神经元的生物特性。
更耐人寻味的是,当知识体系达到某个临界规模时。
会产生类似知识引力的效应。
新知识的获取反而会压缩旧知识的存储空间。
这项研究直接挑战了传统教育学的理论基础。
楚衍对OPERA实验的深刻剖析。
对冷核聚变争议的精准解读。
甚至对暗物质探测数据的微妙把握。
这些远超普通科普主播的专业素养,并非偶然。
他的灵魂深处,镌刻着前世的记忆。
2011年OPERA实验公布超光速中微子数据时。
他恰好在现场。
那天,他亲眼目睹了学术界的集体癫狂。
有人当场宣称要改写物理教科书。
也有人愤怒地指责实验组哗众取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