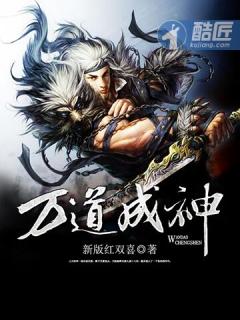鹅绒锁>装疯后美人他要和我he > 第 88 章(第2页)
第 88 章(第2页)
婆子再没来过。据说她真的告到总管面前,灰头土脸,膝盖一软,喊着冤枉。原是想着主子不在,自己打小陪着夫人,和夫人关系极好,定能为自己做主。
哪知实在不巧,那日偏生来了位客人。他来找主子,没找到,正准备出门,却是见到这一幕。总管大感丢脸,还好宋公子不计较,只说“来日再会”。夫人听了什么都没说,两日后,婆子自愿去了别馆。仆从闻到风向,噤若寒蝉,安静不少。
没了婆子打搅,接下来的几日,牧归老老实实地待在屋子里,直到侍女来找她,说外头花开得极好,让她出来走走。
“夫人的意思,怎敢不从,”牧归一笑,将琵琶收好,“劳烦二位姐姐带路。”
侍女指了一个方向:“一直往那走,见着亭子就是。”
澹台家连一只鸽子都飞不进来。婆子之事后,仆从大换血,那几日门前每天都停着车马,下车的欢天喜地,上车的哭天喊地。
夫人没禁她们的足,但谁都不愿做出头鸟。
牧归听着少女清脆笑声,觉得自己终于有了点活人气。
亭子四面落了帘子,外头又摆了屏风。牧归挑帘进来,二人笑容一僵,细细打量过她的脸,才松了身子,放下茶壶水盂,拉牧归坐下。
她们都是金陵人,背景不算深厚,王姑娘家里从商,做些布匹生意,另一人的哥哥在朝中当差。
“朱姐姐,你的画我瞧过了,意境极美,但线条勾勒之下,又带着杀气。上头那些最顾忌这个,我这位置本该是姐姐的。”
杨姑娘指甲染得通红,侧面瞧着又有些发蓝。
“别提这个。早些时候我问过厨子,说今日做了新样式,但是没人吃过,不知滋味如何,还不敢拿给夫人。我央她给我留了一份。现在应该送来了,”王姑娘拍了同伴,嗔道,“不知谁送的,瞧着快一个时辰了,还没送到。”
能叫得动小厮,她们的位置比自己高许多。
一亭子三个人,就她不知。
二人在牧归来之前聊了许久,牧归不接话,便你一言我一语地说上。说了一会,觉得不太对劲——怎么少了一个人?
再一看,却是松了口气。原来牧归只是瞧着某处太过忘神,呼吸声微,她们几乎听不着,无意识间将其忽略了去。
二人对视,王姑娘笑道:“姐姐在看什么?”
“看柱子。这块的纹路着实奇特,我从未见过。”
二人跟着看去,看着柱上刻着的花纹,齐齐笑道:“姐姐,你糊涂啦,这是澹台家的标识呀。”
牧归一愣:“什么?”
“他们常用在铺子上的,书信也会用。姐姐瞧,那也有。”
柱上,桌上,炉子底部,均有类似花纹。
类似,但和她那块玉不同。
“这和我见过的不太一样。我见过的那个,这个位置要往里收一些,瞧着像风筝。”
“可是他们一直用的这个……”杨姑娘眨眨眼睛,一拍脑袋,“姐姐是不是拿到过澹台家的玉佩环扣?”
“有何讲究吗?”牧归反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