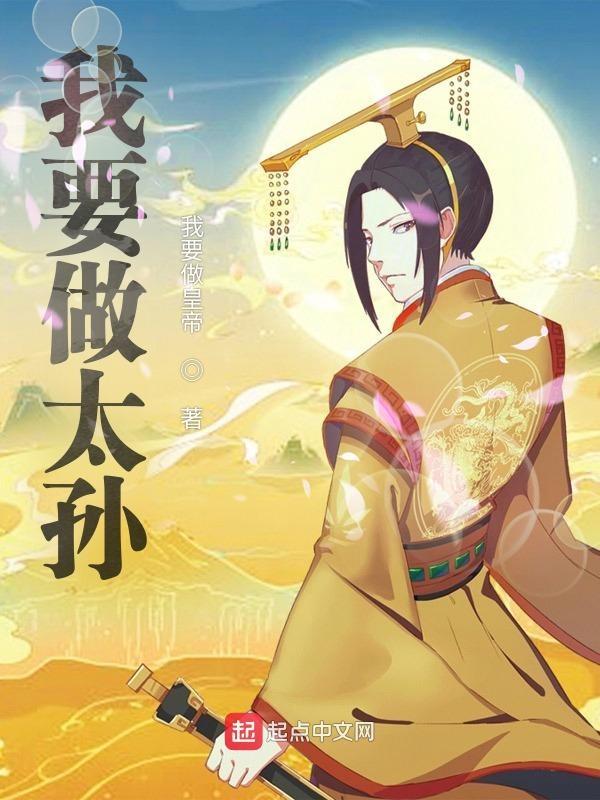鹅绒锁>如意天机棍 > 第7回 蔡昌义只身赴恰城 华云龙携母探师尊下(第4页)
第7回 蔡昌义只身赴恰城 华云龙携母探师尊下(第4页)
诸子百家无不涉猎,尤喜历代史家之作,一部《资治通鉴》更是颠倒看了上百遍,常爱指点江山,臧否人物。
儒学虽未世之显学,这位三斗先生也是科举入仕,却常常对孔圣人有不敬之词,尤对程朱更是不屑。
因生性豪放,不把同侪放在眼里,很快就得罪了不少同僚,以污蔑圣贤,散播异端之罪,革去功名,永不录用,并被打进大牢,后遇先皇登基五十年大赦,才回归故里。
文慧芸和白君仪素问茅东方才名,多次相邀,在华云龙五岁时赴落霞山庄教导华云龙及其姐妹,说起来华云龙无视传统伦理,气吞山河的豪情,固然有天性和家学的原因,母亲的耳濡目染,这位茅先生的影响也不容小视。
三年前,因为妻子多病,加之华云龙已经学业有成,遂还归故里。
母子二人策马向乡下疾驰,太阳已经快要下山了,但见远山如黛,云霞似画,牧笛声中牛羊下,茅舍竹篱三两家。
很快来到一处茅舍,一道清渠从舍边流过,渠边植着几株垂柳,舍前舍后,插着几根翠竹,种着几径黄花,院落中一棵银杏高大挺拔,正是茅东方的住所。
华云龙和白君仪翻身下马,轻叩柴扉,却听得身后床来铃铛声,一人骑着一只毛驴翩翩而至。
华云龙见了,慌忙下拜,口称:“学生拜见师父。”
那人慌忙下驴,扶起华云龙,道:“原来是少奶奶和公子。龙儿快起,你知道师父素来最不喜世俗礼仪。”
“长大了,三年不见,成帅小伙了!”
茅东方拉着华云龙的手上下打量。
“少奶奶和龙儿怎么到了这里?”
白君仪道:“我俩到南方去,路过此处,顺道来看看师傅。”
华云龙道:“师母贵体可安康?妈妈给师母带了块杭州的绸缎料子。”
茅东方闻言黯然,道:“你师母春天已经过世了。老让你们牵挂着,每年都要松懈钱粮过来。”
华云龙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将来我有了孩子,还要请老师教导。”
茅东方应道:“只要为师这把老骨头能挨到那时候,当然没问题。”
华云龙道:“一会儿还请师父带我去师母墓前祭奠祭奠。”
茅东方叹道:“人死如灯灭,你师母死后,我把她火化了,骨灰就埋在那银杏树下。”
华云龙和白君仪跟着茅东方进入院子中,只见银杏树下插着一块木牌,上边龙走蛇形,写着几行字:公孙之树,爱妻之墓。
来自黄泥,还归尘土。
千载银杏,香魂永驻。
叶生晨露,清风絮语,思念在心,天堂在树。
华云龙和白君仪静默致哀,又取出绸缎,挂在银杏树枝上。
已近傍晚,白君仪挽袖下厨,乡间房前舍后多的是新鲜菜蔬,白君仪挽袖下厨,烹饪了几个时令小菜,华云龙打开从县城沽来的美酒,师徒俩开怀畅饮,谈天说地,谈古论今,不亦乐乎。
酒后,师徒二人兴致正高,遂至书斋中继续高谈阔论。
华云龙见师父案头放着厚厚的几卷书籍,封面竟是弯弯曲曲的蝌蚪文,翻开书页问道:“师父这在研究什么天书?”
茅东方道:“这不是什么天书,是西方圣人的经典。你是不是觉得这些像蝌蚪文,其实不然,这些是拉丁文,是万里之外西方的文字。这是两千多年前古代希腊的圣人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也有翻译成中文的,可惜之翻译了一部分,欧几里得比我们的孔圣人晚不了多少;这是一个新圣人,不列颠岛国一个叫牛顿的写出来不久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过去我能总以中央大国自居,视他国为撮尔小邦,实际上西人有很多我们不如的地方,如严密的逻辑,对事物本质深入的思考,不像我们,把太多太多的精力花在表面形式上。近二百年,西人更是在进行一场轰轰烈烈的开启民智的运动,如果我们还继续闭关自守,以老大自居,恐怕过不了很多年,就要落后挨打。”
“师父,那要读这些西方经典,了解西人的思想,是不是要先学拉丁文?”
“是。”
“那师父可愿教我?”
“我这点还是在京师时跟一位传教士,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洋和尚学了一年,这点水平还不足以教你。最好你将来到京师,去跟洋和尚学习,免得我教走样了,误人子弟。”
“那还要师父给引荐引荐。”
“无妨。对你们这些武林世家,师父有句话未必中听,但还是要说给你。西方现在战争都纷纷采用火器,刀枪棍棒已经逐步退出历史舞台,我看这是个趋势,要多加留意。”
“可前朝也装备不少火器,最终还不是败给了本朝的骑射。”
“我知道你们武林人士心中肯定不老情愿,但这是发展的必然。一方面现在火器又有了很大发展,威力更大,射程更远,精度更高,前朝火器败于骑射的原因,还是跟训练不够,战术不对头有关,更重要的是国人不懂几何,所以首先在射击精度上就差了很多。”
是夜,师徒俩秉烛夜谈,直至四更,方才睡去。
第二天一早,华云龙和白君仪向茅东方辞行,风尘仆仆继续向南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