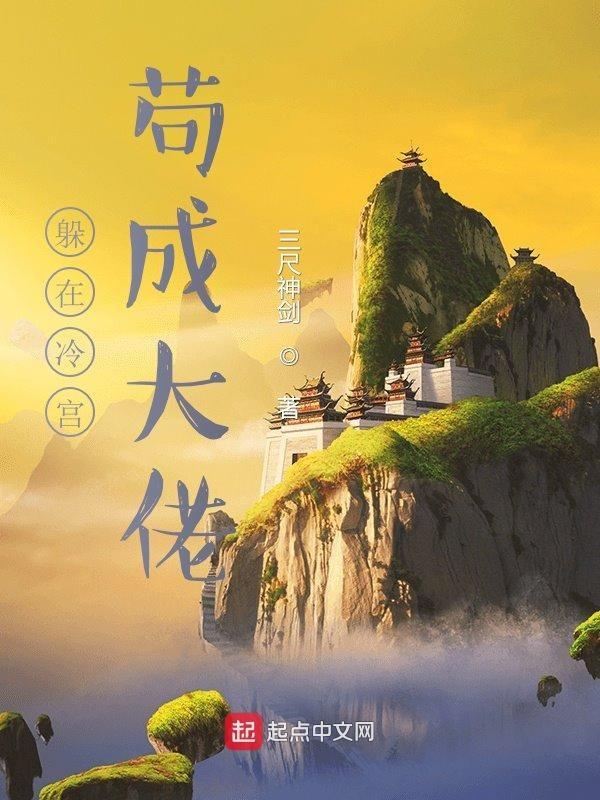鹅绒锁>惹错世子后 > 第 17 章(第1页)
第 17 章(第1页)
谢绍辰垂眼看着咬住他手指的女子,点点湿润晕染在指腹,如同在陈年的老茧上涂抹一层果蜜。
女子咬得力道不小,疼痛开始蔓延,可他没有排斥,甚至觉得微妙。
怪异感袭来,他高挺的眉骨渐渐隆成川字,继而扣住她的后颈,迫使她扬起脸。
云朵簇霞光,妍姿艳质,粉面朱唇,唇角一丝血迹,衬得唇色娇艳欲滴。
谢绍辰替她擦去,没再施以报复。
将人抱下书案,他牵起她的手,熄灭烛台,慢慢走出公廨。
叶茉盈怔怔望着斜前方的男子,愈发琢磨不透他在这段姻缘中的想法。
释然了,破罐子破摔?
“夫君。”
“嗯。”谢绍辰慢下步子,看向斜后方。
叶茉盈加快步子,与之并肩,犹豫片刻,道:“近来有心事吗?”
总觉得他清绝的气韵中多了一丝忧郁,人是压抑的,又隐隐在自我纾解。
讳莫如深。
谢绍辰轻笑,身形轮廓在月下变得柔和,他没有回答,握着她的手安静走进寝所。
将近寅时,夜未央,满天星辰笼罩大地,已经“睡”下的男人抽出被妻子搂住的手臂,执灯走出房舍,独自坐在屋顶上,望着江宁的方向。
天蒙蒙亮,一人一马提前出发,踏上前往江宁的路途。
宝蓝衣衫在晨风中猎猎作响,犹如深海浪潮的色泽。
青年依旧跨坐那匹堂兄赠送的骏马,一人一马斗智斗勇。
“右右右。。。。。。吁!”
“噗。”
黑亮的大宛马不耐烦地扭了扭脑袋,被背上的青年扶正长长的脖子。
谢翊云好声好气地哄道:“好马儿,咱们继续赶路,等到了驿站,也好吃些青草、麦秸。”
他抚了抚马匹油亮的毛发,猛地一夹马腹,继续前行。
被顺了毛,大宛马哒哒哒奔驰在崎岖小径,发挥出汗血宝马的优势,踏飞燕,如履平地。
扬州距离江宁不远,谢翊云是在容易困乏的晌午进城的。
守城的将领查过路引,立即派人前往布政司请示,不出两刻钟,一辆马车停靠在青年面前。
官居通判的绮国公谢伯懿和官居提刑按察司佥事的二爷谢仲礼一同前来,齐齐打量着站在艳阳中的青年。
“伯父。”
“父亲。”
谢翊云依次请安,扬起笑脸,灿烂明艳。
绮国公递出手,拉青年登上车廊,又命人牵过青年的大宛马,“侄儿怎么也喜欢独来独往,身边连个伺候的扈从都没有?”
这一点,与自己的儿子极像。
谢二爷哼一声,“他啊,没有享清福的命。”
比起爱说笑的国公爷,谢二爷严肃许多,浓眉入鬓,虬髯墨黑,拒人千里。
可自家父子撂下帘子哪会生分,谢翊云揪住老爹一缕卷翘颊须,笑嘻嘻道:“爹爹忘记娘亲的叮嘱了?多笑笑,十年少。。。。。。诶诶。。。。。。”
被自家老爹赏了一脚,青年抱拳咳了咳,看向盈满笑意的大伯,“让伯伯见笑了。”
伯伯比伯父听起来更为亲昵,谢国公朗笑一声,拍了拍青年的肩头,难怪这小子更得宗族长辈的喜欢,有着经年不变的热情和爽朗,是自家儿子不具备的。
“布政使和按察使都在等你呢,伢子出息了,待会儿见到两位大人,可要好好表现。”
在谢国公眼里,后辈永远是孩子,一句伢子,充满慈爱。
谢二爷又是一哼,“老子不求他好好表现,谨言慎行就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