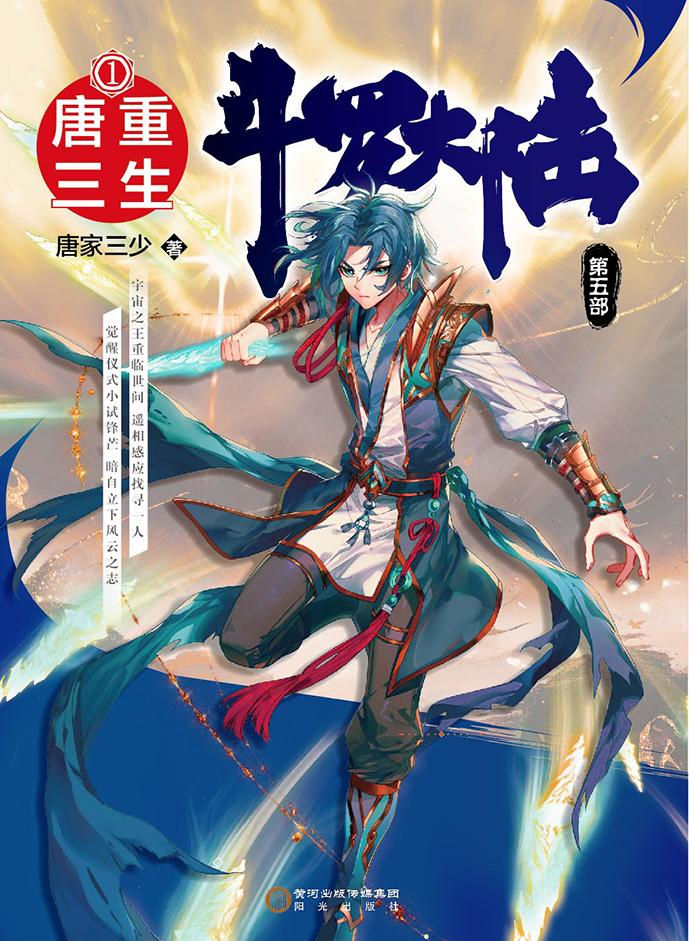鹅绒锁>黎妃传 > 第087章 归去(第1页)
第087章 归去(第1页)
九月二十七,朝歌。
天空是阴沉的,像蒙了一层浮灰的琉璃,厚重的浓云直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正是阴雨连绵的深秋,午后的空气潮湿、黏腻,仿佛能挤出一汪水。
秋风拂过满城枯叶。
城西,一名传令兵小跑着来到城墙下,按着岔气的腰腹急促地喘息。
这里刚刚经历了一场大战,可谓断壁残垣。
——还是来晚了吗?
咸涩的液体渗进眼眶,他弯着腰抹了把额上细汗。因为跑得太急,松松垮垮的战袍湿答答地黏在身上,被风一吹,更添几分凉意。
登楼的台阶很高、很窄,需要扶着塌了一半的砖墙——上面沾着暗红的灰土,被接连的落石砸出坑洼不平的凹陷。
路上歪倒着横七竖八的、残缺的躯体,胸口插着乱箭,已然没了生息。
猩红的鲜血喷溅而出,似乎还带着滚烫的温度。
战况惨烈,触目惊心。
传令兵强压下翻涌的心绪,战战兢兢地将视线移向高处——
城台上,有个人影披着黑袍迎风而立。
他站在遍地横尸中,清俊的身姿依旧挺拔;手里握着面残破的旗帜,绛紫织料上依稀能辨认出半个“黎”字,还在桅杆上高高挂起。
城楼下是披坚执锐的北梁铁骑,数千名弓兵搭箭在弦、蓄势待发。
显然对方也没料到,那样尊贵的大人物居然放下身段亲自守城,乃至束手无策。
双方不知对峙了多久。
周围很安静,静得能听见风过树梢。
“……大人。”
传令兵试探着开口,一时不敢上前。
被几千张连弩瞄准心脏,那位大人连睫毛都没颤,清冷的嗓音如流淌的银泉:
“报。”
传令兵像被这字眼惊醒似的,他深吸一口气,过了很久才找回自己的声音。
“今天鸡鸣的时候,梁军在城北发动了又一轮突袭,守城军官、士兵三十五人,还有姜统军……全部遇难。”
那人微微蹙眉:“姜楠?”
“姜统军……”传令兵提到这个名字便哽住了,竟忽然不知该怎样开口。他站在那里,声音发紧,只觉城楼上的风很冷很冷:“姜统军为保护一个孩子,中了流矢……他、他让我转告您……”
传令兵慌乱地瞟了他一眼,断断续续道:“空缺的城防已经有二十个人补上了,工匠们正在修补城墙,让您,让您……不必担心。”
。
洛月听完闭上了眼。
。
“吾知道了。”
。
长风吹度万里,吹皱了斑驳的旌旗,吹乱了他满头的白发。
御河蜿蜒流淌着绕城而过,被守城将士的鲜血浸染,早已不复清澈。
洛月就那样静静地站着,仿佛对岸的千军万马都化作了无形的空气,仿佛世间一切的一切都与他再无关联。
过了很久他终于抬眼,却见传令兵依旧站在原地,双手攥着衣角,似乎完全没有离开的意思。
他疑惑地望了过来,没有说话。
“我……我要留下来。”传令兵咽了口唾沫,垂着眼始终不敢看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