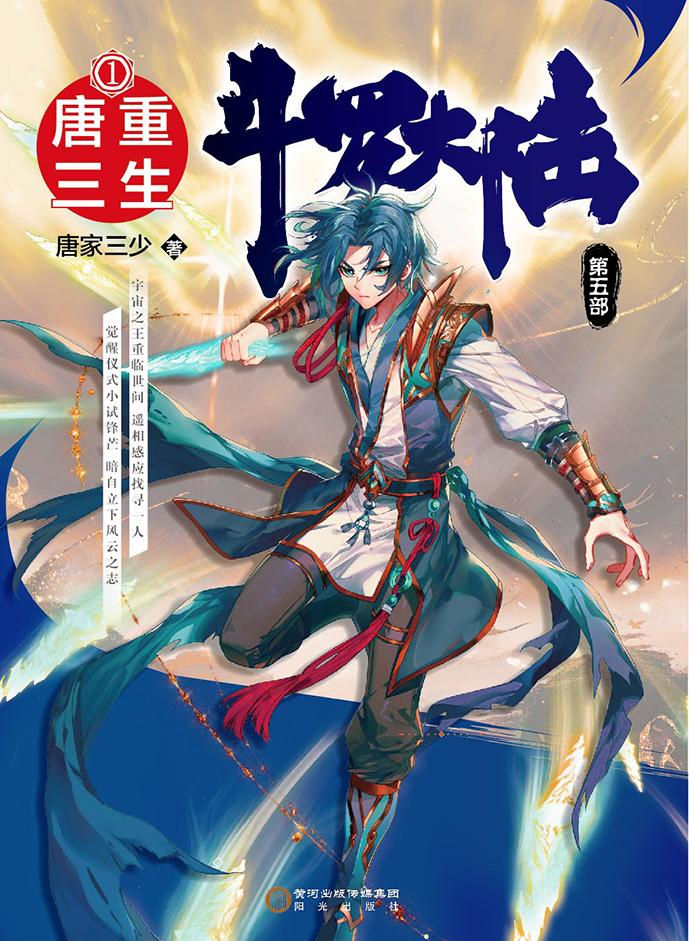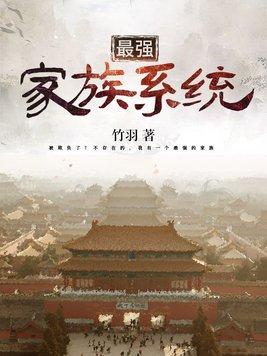鹅绒锁>仙母种情录 > 第4章 偷香窃玉(第1页)
第4章 偷香窃玉(第1页)
数十年打熬的一副铮铮傲骨,费尽心血、破而后立才铸成的稀世功体,却敌不过倾城仙子短短一句爱语,好似风中絮那般不堪一击、剑下帛那般应声而裂。
耳旁拂过娘亲的兰息,身体如遭雷击般,竟好似筋软骨酥了,一股眩晕感冲上天灵:“娘亲!”
“霄儿急什么,晚些时候娘自会好好服侍霄儿——但不能真个销魂就是了。”明明是犯禁悖伦之语,娘亲却好似浑不在意般顺口说出,但那双剪水明眸中的宠溺又不曾离开过爱子半分。
这般仙颜圣洁而又口出旖语的神态,教我心头的爱欲之火腾腾叫嚣,理智转眼便如泥牛入海般消失不见!
我情不自禁便要扑倒娘亲,什么人言可畏、雄风难起都抛诸脑后,只欲与眼前的仙子鸾凤和鸣、共效于飞!
然而,我双眼一凝正欲唐突冒犯,却被笑吟吟的仙颜抚平了大半欲念,长舒了一口热气,苦笑道:“娘亲你就别捉弄孩儿了——此时此刻,孩儿又不能把娘亲'就地正法'了。”
“霄儿若是真急于一时之欢,娘也只好惟命是从了。”仙子似是对色迷心窍的爱子无可奈何,螓首稍低,玉手将鬓颊侧的青丝一捋至尾,端坐娴静,风情姿韵恰似低眉顺耳的闺中少妇般,既幽怨又逢迎,如何不教人欲火焚身?
毋庸置疑,娘亲此番爱语相逗,虽有几分撩拨,但倘若我真把持不住,她也必会放开身段,与我温存亲近一番——哪怕光天化日也义无反顾。
但也正因娘亲为爱子甘冒奇险,我才更不能得意忘形、胡作非为,哪怕院落中没有多余的耳目也不能掉以轻心。
然而,瞬息之间,我还是几番挣扎,几度难以自持,最终艰难低头,端起饭碗,眼观鼻,鼻观心,闷闷道:“孩儿把持得住——娘亲不懂事,孩儿得懂。”从前我只想与娘亲双宿双飞、巫山云雨,此时面对仙子毫无保留地爱意与宠溺,受元阳损耗、人前守礼之限,竟是只能暂避锋芒,心中多少有些世事难料的郁闷。
“好你个霄儿,竟打趣起娘来了~”娘亲在我肩上轻轻一推,呵呵一笑,心平气和道,“好了,娘不逗霄儿了,吃过晚食,霄儿便回房歇会儿,好好体悟一下方才所得。”
“是,娘亲。”我这才长舒一口气,抬头与娘亲相视,不解道,“娘亲为何忽然决定今晚要服侍孩儿?”虽然娘亲方才确实在与我撩拨逗趣,但也并非全是信口之辞——至少我万分确定,“夜闺温存”是仙子心中斩钉截铁的决断,不容更改。
仙子将一块精肉夹至我碗中,宠溺而满意地微笑:“霄儿今日武学有悟、甚有所成,娘自然要给霄儿点甜头尝尝了。”
“原来如此。”绝代无双的仙子要与我一番亲热温存,我自然求之不得,但转念又愁道,“可孩儿……”我还未言明,仙子已然会意,微笑摇头:“不妨事,娘自有办法。”我正欲追问有何解法,却忽然灵光一闪:“娘亲,莫非是……”
“不错,届时娘会以冰雪元炁护住霄儿阳脉,便无虞动欲引伤了。”娘亲心有灵犀地颔首,也不藏着掖着,反似觉孺子可教地一脸欣慰,“虽然不可长久频繁,但今日事出有因,偶尔破例也无伤大雅。”
“原来如此,孩儿先谢过清凝的一片好意了。”解开心头一点疑惑,唯恐再次引火烧身,我也不敢在此事上深想,转而夸赞起了仙子的手段,“娘亲的冰雪元炁,既可用于惩罚宵小之徒,又能让擒风卫折腰屈首,还可保孩儿尽享温柔,当真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呐。”仙子双眸微阖,颔首浅笑道:“不错,就似霄儿今日顿悟所得之理一般。”
“对了,孩儿听沈师叔说娘亲还可做到元炁破体,如此说来,娘亲方才与孩儿练招还是留手了?”
“确实如此,不瞒霄儿,若娘用上先天之能,霄儿连出手的机会都没有——当然,天下武人,若未至先天之境,一旦遇此元炁破体皆要束手就擒。”虽知娘亲从不骗人,但仍有半分不可置信:
“竟有如此神奇?当年娘亲亦是倚仗'破体元炁'连败剑玄宗三十五人?”
“那是自然,娘何时骗过霄儿?不过娘连败剑玄宗三十五名门人,倒并非纯以破体元炁破敌制胜,只因娘彼时虽然已有先天境界,但未至炁体同源的地步,还不能随意频繁地运用。”娘亲既宠溺又嗔怪地在我鼻子上刮了一记,而后又轻轻颔首,细解当年之事,“且霄儿有所不知,剑玄宗的'铸剑大典'讲求的是'以巧破巧',而非'一力降十会'——娘若以此败了他们,不过是以境界压人,那执剑人也不至于自觉宗门无光,进而不顾身份地以大欺小了。”我点点头,忍不住蹦出一句挑逗之语:“原来如此,孩儿的清凝竟有这般厉害啊!”仙子闻言,双目微眯,凝视着爱子,带着'勿谓言之不预也'的神色,抚着肩头青丝,好整以暇道:
“嗯?这可是霄儿撩拨在先,可不要怪娘……”
“孩儿错了!”仙子风情,我素有所知,哪敢久逞威风?于是连忙举旗献降,埋头用膳,作狼吞虎咽状,只盼娘亲就此鸣金收兵。
“瞧你,急什么?娘还能吃了你不成?。”仙子好似真被爱儿所骗,反以玉手轻拍我的背部,柔言婉语,似在担心饥不择食的幼子忙中出错,“慢些吃,别噎着了”我这才舒了一口气,咽下口中肉食,抬头傻笑两声:“那自然是不能,娘也不舍得吃了孩儿。”
“贫嘴~”
一顿打趣后,母子二人再无波澜地用完晚膳,便至天色渐暮,我与娘亲草草告别,各自回房歇息。
将含章挂在床头,望着再无外人的卧房,我却心头渐渐燥热。
虽说眼下难振雄风,但仙子绝妙胴体与婉意逢迎令人枯骨明显,我闭目间便是娘亲在床笫之间的情态,一举一动都风情万种、一吟一啼都妩媚婉转。
哪怕元阳大损也难以自制,多少存了“若能再亲芳泽,即便精尽人亡也在所不惜”的纵欲之念。
当真应了那句浪荡之言: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
眼下未至宵禁之刻,若放任此等欲念嚣张,恐怕要度日如年了,我只好盘膝打坐,费了好大一番功夫,才祛除杂念,平心静气地行功练炁。
好在永劫无终的功法特殊,进益卓然,不知不觉便专心致志于练炁,直至更夫报时的锣声隐约传入耳中,我方才从入定中脱离,果见天色已深、不见新月,约是戌时了。
我起身关好窗户,吹灭烛灯,想到自己将欲践行之事是何等悖逆人伦、违反纲常,一股难以言喻的滋味从心头升起,既兴奋又畏惧,既踌躇又刺激。
我深吸一口气,仗着多年武学基础,悄无声息地行至门边,探头向外瞧去。
楚阳的拂香苑不比百岁城,既无侍女日常扫洒,也无匠工修葺养护,因此廊下并无灯笼高挂,东厢只有一点灯豆,应是娘亲所居,而西厢及正房中均无灯火,常人难以辨清庭中实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