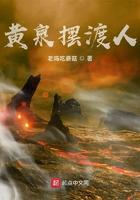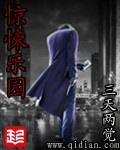鹅绒锁>破落户一朝逆袭之我靠五个儿女扬眉吐气 > 第九十五章 高中会元二(第1页)
第九十五章 高中会元二(第1页)
第二天考的是"农桑振兴策"。这个题目正中大郎下怀。杨家虽然经营茶肆,但在乡下仍有几亩薄田,大郎从小跟着佃户下地,深知农事艰辛。
"农为国本,然今之农具笨拙,耕法陈旧……"他写道,"当改良犁铧,使深耕易耨;推广轮作,以养地力……"
写到一半,忽然一阵腹痛袭来。大郎脸色发白,想必是昨夜的冷雨着了凉。他强忍着不适,继续写道:"江南可推广稻麦轮作,北方宜种耐旱作物……"每一个建议都有实地考察为依据,而非纸上谈兵。
午后,主考官周大人带着随从巡视考场。这位年过六旬的老臣以严厉著称,所到之处考生无不战战兢兢。当他停在大郎号舍前时,大郎正全神贯注地写着灌溉系统的改良方案,竟未察觉。
周大人眯起眼睛,看着这个瘦削却挺拔的年轻人笔下流出的工整字迹。他悄悄站了半刻钟,直到大郎写完一段抬头,才惊觉考官就在眼前。
"学生失礼了。"大郎慌忙起身行礼。
周大人摆摆手,拿起他的考卷浏览。渐渐地,老人花白的眉毛扬了起来:"这水车联动之法,你是从何处学来的?"
"回大人,学生外祖家有位老匠人,曾造过这种水车。学生亲眼所见,一架水车可灌溉二十亩地。"大郎恭敬地回答。
周大人不置可否,放下考卷离开了。但大郎注意到,老人的脚步比来时轻快了许多。
第三天是诗赋考试。虽然疲惫不堪,但大郎的文采反而更加飞扬。他写江南水灾后的重建,写农民盼望丰收的喜悦,字字真情实感。当最后一个字落笔,他长舒一口气,眼前一阵发黑,差点栽倒在号舍里。
收卷的差役到来时,大郎的考卷已经整齐地捆好,上面还细心地盖了张油纸防潮。那差役诧异地看了他一眼:"小郎君倒是细心。"
大郎虚弱地笑笑:"寒窗十年,不敢有丝毫马虎。"
走出贡院大门时,暖阳照在脸上,大郎恍如隔世。他摸了摸胸口的平安符,心想不管结果如何,总算没有辜负父母亲和姐妹们的期望。
而在阅卷房里,那位与大郎有一面之缘的周大人正拍案叫绝:"好一个'以工代赈,既治水患,又安民生'!此子不仅文采斐然,更难得的是见识卓远。"
副考官凑过来看:"下官刚才阅到一篇农桑策,提出'因地制宜,不可一刀切',倒是与周大人常说的不谋而合。"
"拿来我看。"周大人接过考卷,眼睛一亮,"果然是同一人所写!你们看这笔字,端庄而不失风骨,内容更是字字珠玑。"
几位考官传阅着大郎的考卷,赞叹声不绝于耳。当拆开糊名处时,周大人抚须微笑:"杨瑞华……当真是个好名字。此子当为今科会元无疑。"
一个月后,喜报传来,大郎——现在该称杨会元了。这会儿,夕阳西斜,金色的余晖洒在茶肆后院的菜地里,泥土泛着湿润的光泽。
杨大郎挽着袖子,裤腿卷到膝盖,正弯腰在菜畦间除草。他动作利落,手指拨开翠绿的菜叶,将杂草连根拔起,丢进一旁的竹篓里。
汗水顺着他的额头滑落,他却浑然不觉,神情专注得仿佛这不是一块菜地,而是他笔下策论里的锦绣文章。
忽然,前院传来一阵喧闹声,紧接着是阿福急促的脚步声。
"大郎!大郎!"阿福气喘吁吁地跑过来,脸上涨得通红,手里攥着一张烫金帖子,"喜报!喜报来了!"
杨大郎直起身,擦了擦手上的泥土,眉头微蹙:"什么喜报?"
"会试放榜了!您中了会元!报喜的人就在前头等着呢!"阿福激动得声音都抖了。
杨大郎神色依旧平静,只是眸光微微一动,随即又恢复如常。他拍了拍手上的土,淡淡道:"知道了,你先去招呼着,我换身衣裳就来。"
阿福一愣,本以为大郎会欣喜若狂,没想到他竟如此淡然,只得应了一声,又匆匆跑回前院。
杨大郎回屋换了件干净的青布长衫,这才缓步走向前院。报喜的差役正站在茶肆门口,手里捧着大红喜帖,周围已经围了不少看热闹的街坊邻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