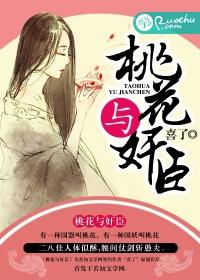鹅绒锁>与宿敌成婚後 > 第180章(第1页)
第180章(第1页)
迎着众人错愕的目光,姜时愿移步入殿内,她馀光觑见她的夫君被禁军以利器包夹在其中,更听他的嗓音清越带颤,「阿愿。。。你为何要来?你不该来的。」
姜时愿抬起一双琥珀色的眼眸直视君王,温婉的声音层层荡开在大殿之中。
「洛阳姜氏嫡女姜时愿见过陛下,臣女来替姜家鸣冤。」
「同时,臣女也要替夫君伸冤,夫君从无不臣之心,日月可鉴丶
天地可昭!」
左相看见姜时愿凌厉的目光移向自己,从青袖中缓缓掏出早已泛黄的信纸,面色再不能稳住,黑得几乎能泛出来,手中的芴板也「咔」碎出细纹。
两只纤浓得宜的玉臂缓缓高举信封,试图以淡薄的一人之力呈于帝王眼下,群臣眼下,还有千万双世人的眼下。
姜时愿伏跪在地,重磕在地,青丝也散乱在肩前和冷砖上。
泪水慢慢晕染青衫,咸淡酸涩的血泪漫入唇腔之中。
她双眸殷红,嗓音压抑至沙哑,却字字铿锵,「姜家一直效忠陛下,兄长姜淳也从无谋逆祸心,这一切都是左相的设计陷害。臣女的兄长忠君爱国,至死都想为大庆扫除馀孽,冒死藏匿此密信,才因此遭受了杀生之祸!」
姜时愿颤抖着一双柔荑将密信慢慢摊开,高悬于自己的头顶,浑身战栗,「洛州御史大夫沈煜曾书写密信一封,信上皆是弹劾当今左相。沈煜发现天外天以赌宴为名明面上肆意敛财,实则暗中替暗河培养杀手。而沈煜进一步调查,发现天外天和暗河积攒的脏银一部分流出偏远之地招兵买马,另一部分则全部流入左相府。」
姜时愿一双含恨的眼眸如剑刺向左相,汗珠在额间凝集,是她愈发不可掩藏的杀意。
「而我的兄长翰林学士姜淳,曾是您的学生,前往左相府中送拜帖之时,因是偶然间发现了这份密函,所以秘密将密函窃走,藏在姜家。而你发现密函不再又询问了下人今夜有谁来过后,自然而然把嫌疑定在我兄长的身上。」
「于是,你不惜以身入局,设计陷害兄长谋杀燕王,并想借着圣人的旨意查封姜家,目的就是想找出这封密函。」
「而你却没想到你翻了整个姜家,却依然没有发现密函的下落。」姜时愿笑意很冷,「估计左相至今仍不清楚这封密函藏在了何处吧?」
左相目光紧盯着姜时愿手中的密信,脸色黑如铁铸,又抬眼扫上高位,气息急促。
姜时愿眼中炽热的怒意在烧,眼中噙着的不再是泪,而是三年日以继夜的恨,国雠家恨。
她嗓音虽软,却竭尽全力,声震大殿:
「还请陛下过目忠臣沈煜不惜以命写下以及兄长以命护下的密函,密函上罪证清晰,左相辩无可辩。」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崔广事领了庆帝的示意,脚步踉跄地滚下玉阶,接过姜时愿手中的密函转而呈在圣人的面前。
少许之后,圣人面色红云,竖眉冷峻,一声怒喝,喝得崔广事和身旁的祁王燕王皆跪了下去。
庆帝指着左相,胸臆如堵:「你好大的胆子!来人!擒住他!」
左相自知无力回天,已成败局,放声大笑,抬手撕去了许久的人皮面具,露出他原本的真面容。见之,庆帝差点稳不住声,扶着龙头,满眼仍是不可思议,「孤见过你,当真是你!你就是那个楚国国师!」
「就是老夫!」左相声嘶力竭地直指九五之尊,淬着最恶毒的话语,「你个狗皇帝灭我楚国,杀我国人,你为何还能夜夜安睡,为何还有脸高居这个位子!老夫要拉你下来,要让这个天下归还给我楚国!」
「放肆!」群臣怒喝,「来人擒住他!」
而左相依然不慌不忙地转过身,双眸血红,不过是抬手之瞬,方才包夹上的禁军尽数倒地丶血流成河,他如同个疯子仰头大笑着臭虫烂虾的无能,温热鲜红的血飞溅至高洁的金殿之上。
再无阻拦,左相又步步朝着谢循而去,满是嘲讽:「阿循啊,你还真是个养不大的狼崽。你就算救了庆国万民,帮了这个狗皇帝和百官,你以为他们就会对你感恩戴德吗,就对你既往不咎吗?」
「呵呵呵。。。」左相的鼻腔里哼出冷笑,摇着头,「你还是太天真了,阿循。我的下场就会是你的下场,懂吗?」
一群禁军倒下,很快又紧接着又玄甲鱼贯而入,放眼大殿之外,千万人拿着兵戟相对,左相仰头看着金銮段的牌匾痴痴地笑着,自知已无活路,又回头向高位深深忘了一眼,眼眸里倒映出楚国的山河社稷。
鬓发苍白的左相,笑了,痴了,缓缓移步走向殿外,直面军队。。。
这场厮杀从晨曦持续到黄昏,姜时愿看着满庭血色,甚至连同晚霞都被染得嫣红。
她扶着殿门,看着左相陷入疯魔,以一敌百又敌千,哪怕他已精疲力竭丶身中数刀,却迟迟不肯倒下,大叫着要杀死每一个庆国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