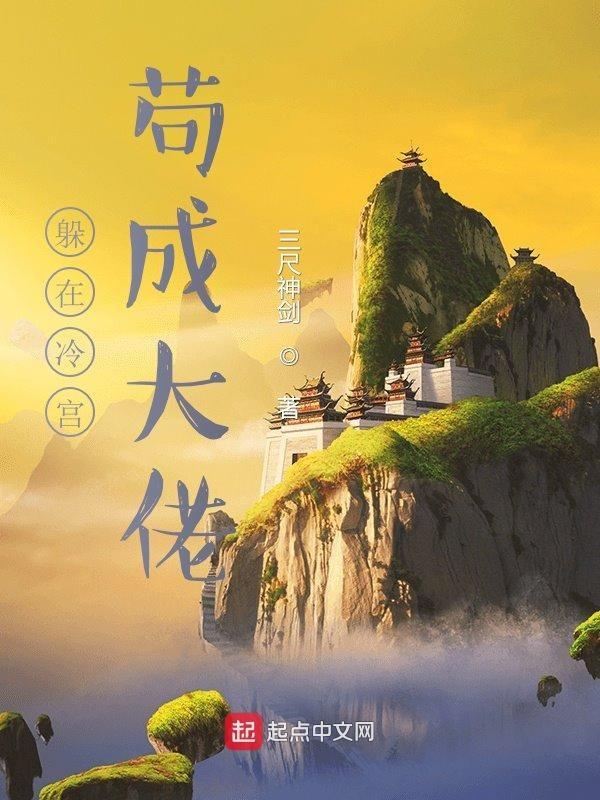鹅绒锁>花荫露 > 第16回 洞房花簇众女心酸(第2页)
第16回 洞房花簇众女心酸(第2页)
余娘听他驾声燕语,委实动听,拿捏亦甚得当,心道:“果是大户人家儿女!”他亦回道:“新人来嫁,老妇劳累些,亦是常情,即肏一间,便不生分,我合公子事体,料贤媳亦知。适才言辞,颇当碍耳,还请贤媳见谅村妇鄙语,只不知出了甚事?可否见示。”
小姐急谓公子道:“大姐进来罢!”
余娘入得花轿,只觉轿里香气氨氛,热气腾腾,又见他俩衣冠不整,鬓斜发乱,心道:果不出我所料。
又见新妇天姿国色,雍容华贵,犹见他一把窄窄溜溜小蛮腰,遂折服忖道:“难怪景儿久肏不厌,只这腰儿。便令千万男人跪拜不起矣!”乃赞曰:“我儿果得佳妇。如此良人,夫复何求!”
小姐见大娘体态丰腴,宛新婚少妇,亦啧啧称道:“大娘若二八丽人,小女子勿及也。”
王景听得高兴,乃道:“俱是我的,俱是要我肏的!”
余娘敲他一记响头,骂道:“新人乍见,景儿礼貌才是。”他见他俩无甚不适,遂惊道:“既如常态,有何难堪?”因轿内昏暗,他视那红柱模模糊糊一团,以为公子手捏盖头拉着新娘亲热。
小姐乃道:“大姐勿笑,郎君阳具伟长粗壮,而小女子器具浅薄外露,如今肏得进,却取不出。如何是好?”
余娘见公子掀去盖头,露出根一端粗一端细之长物,他以手把之曰:“此乃景儿肉具,竟复长尺寸又粗几圈。既已取出,何妨?”
公子逐捺开帘子,拍着粗头说道:“我之大物被他包住了,大娘,瞧仔细些。”
余娘仔细看来,只见公子大物外面果然被一皮囊紧紧包住,虽形状立现,但均不见其身,唯见细嫩包友而矣,余娘如视怪物般看小姐一阵,方道:“想我幼年人勾栏,阳具见过不少,阴器又何止百十,只未见过这等吊耳器物。我原道我之物至阔至深,亦算奇物可居,竟不知媳妇竟生如此妙物!从今此后,吾家首推你第一也。”
小姐垂头道:“大娘阅历丰富,颇多技巧。小女子不及也。我物虽奇,却不敢妄称第一也!只须解了今日困境,此物才属我也!”
公子浑不当事,一手拍小姐皮囊,一手探余娘阴户,嘻嘻道:“管谁第一,俱是我人也。”
余娘观摩良久,乃把手捏公子龟头,觉龟头大如碗口,又见小姐阴器颈口约似杯口,便知症结何在,至于阴毛沾联小事,以开水冲洗即解矣,她拎来茶壶,倾温水而淋之,毛皮果自脱解。
公子喜道:“大娘堪称女界泰斗,天下难事,弄巧亦成。”
余娘却摇头道:“公子勿喜,汝物龟头甚大,他户预口太细,须另想它法。”
他把住小姐阴户,亦意公子缩腰后退。
龟头果动,仅滑尺余,暂止,再动,小姐亦随他去了。
小姐惊道:“勿扯,恐破矣!”余娘见轿内狭窄。
乃令他俩出轿,他俩于屋里捣弄一阵,公子大物只不得出。
公子乃道:“着银儿来,上次亏他妙法。”余娘方醒悟道:“只顾瞎忙,忘了他等。”速出,不题。
小姐盈盈一笑,谓公子道:“若女俱来。汝当避之。方不羞尔。”
公子却说:“若我一遍,恐他等挖地三尺亦擒我来。久不合我人,他们渴得上下流水,焉有逐我之意,恐恨不能将依扫地入门矣。”
正调笑间,余娘领着玉娘蝶娘金儿银儿一干妇人喳喳而来。恐他等已知大概。个个脸露兴奋之色。亦笑亦讥。
银儿率先破门而入,视之,惊叹:“又长矣。又粗矣!真一顶门杠也!主母真个赛昭君比飞燕,天下少见!天!生得这等怪器!乖乖!从今日起,若公子爷不陪你睡,我陪小少母?”
金儿不解其意,公女亦惊亦诧,俱咧开红唇不语。
余娘笑银儿:“狗奴才见了新主人就不理旧主人哩!”银儿忽红了脸,忙道:“我见少主母阴器状若阳具,虽一空洞,于那紧要关兴大上一人,亦能泄火解译。正欲陪他睡。”
众女大笑。
只这一笑,大家便是一家人了。
俱作好奇状,上前捏小姐阴户,实乃捏公子巨大阳物也,俱各心道:“几日未见。又壮又长,恐我肏得否!新人真福人也,入得进,便抱了它不放,这等好事,怎轮不上我?”
独金儿知真利害,乃谓小姐:“痛与不痛。”
小姐洒笑,道:“何痛之有?只涨得慌。我那小便洞儿亦在里处,恐被堵死了罢。”众女复大笑。
有诗为证:
花轿慌慌进洞房,且先肏罢再拜堂。
众妇纷纷闹洞房,得见天下第一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