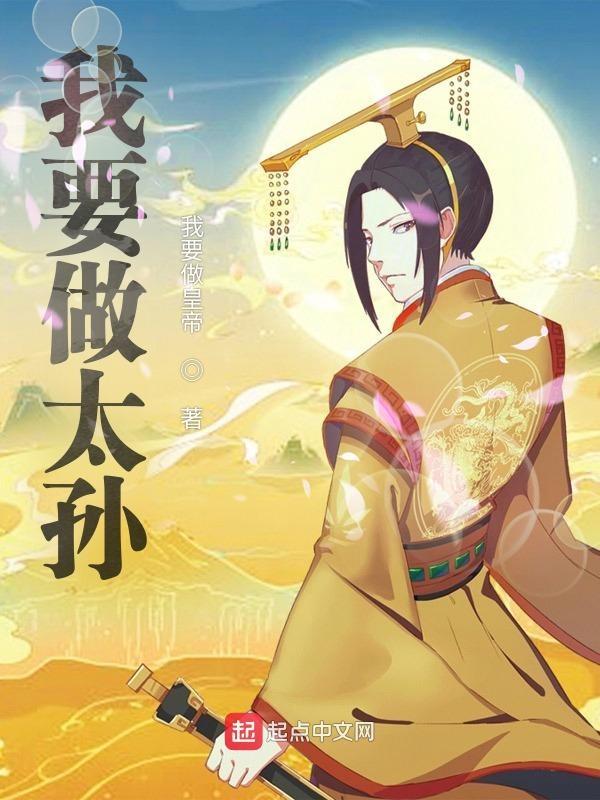鹅绒锁>碧蓝港区的两日小剧场 > 第69章 黎塞留 主教大人的绮思(第3页)
第69章 黎塞留 主教大人的绮思(第3页)
“抱歉啊,黎塞留,”我说,“让巴尔那家伙说,希望你有话直接和她本人说而不是通过别人。
她闻言抬起头来,听我说完却是轻松地笑笑,“并非如此,指挥官。我只是…只是想要成为能够和她好好说话的人类罢了。”
“啊?”
“前些天,我找敦刻尔克进行了商谈。她说,让巴尔抱怨我不曾说着人话。我想,是我过分隐藏内心想法的缘故吧,”黎塞留紧紧揪着胸口的布料,望了过来,“人与人的关系是敏感而复杂的。我自知自己不善于相处,也不擅长表达。我想,变得更加直接一点。”
“那个,呵呵呵,”我干笑起来,“对妹妹的思念我能明白了。但是也不用采用这么极端的手段吧。”
“极端…吗?指挥官可是为我降下了最严苛的审判啊,”她双手交叠,平直射来的目光中浸透威严,“我可以质疑你的权能吗?”
“对不起我错了!”
“请站直了!”她叱道。
“是!”
“您,了解我吗?”她站起身,白裙微微摇曳,如红莲出水,“我抵达这里的那一天。我见到妹妹的那天。我被她拒绝的那天。”
啊,我了解。
她走进窗边白漫漫的光里,衣裙染上辉芒。
她继续说着:“我去酒吧痛饮的那天。我被人用自行车载回去的那一天。我被摸着头安慰上帝也会有两天休息的那一天。”
我…我也了解。
她步进黑暗,金色的秀发沾染上深灰,变得晦暗起来,像是秋野的草。
紫红色的湖水漫来、漫来。
肃然挺直的鼻梁,裸色,不带笑意的唇,柔白的颈子,诱人的红袜,往我的眼睛伸出沉没,坠落。
她继续说着,“那么,我强迫自己忘记的那一天呢?我祈祷忘记的那一天。我连续梦到,终于以借口麻痹自己,站到他面前的那一天呢?”
“我…了解了。”我拘谨地缩缩脖子,代替点头。毕竟,身前已经没有太多的距离。
“很好,”她漠然似地笑笑,忽然抬起手来,像是确认一般,涂染着鲜红颜色的手指木木地摸着我的唇角,“人与人之间的微妙,你领悟地并不算太慢。那么,你当常怀感激一一”
她深深吸上一口气。因为,之后会变得…不大方便。
翌日。
“那个…你可以用‘舒服’代替‘愉悦’吗?听着怪怪的…”
“不好。那样不能体现等级之高。”她一本正经地回答。
“啊,那好吧,”我挠挠头,然后从扔到一边的裤子里摸出戒指,“那个,可以誓约嘛?”
“所以其实我只是为了和让巴尔搞好关系。所以,把你的誓约收回。”她命令道。
“…所以说了啊,那个我没有办法帮助你,”我苦起脸来。
“当然,我只是为了取得一种祝嘏样的恩赐罢了。甚至可能和你无关。”她冷冰冰地看着我说道。
“哈?”
“我也和俾斯麦及天城商谈过了,果然和你做之后,都和妹妹搞好了关系。”她认真地说道。
“那都是巧合啦!根本没有这种联系!”
“可是…可是…誓约之后,你难道不会,”她双手抓着被单,掩在身前,一边向后躲着,“你难道没有想过拘,捆,或者在广场上,面对教徒从后边…”
“啊啊啊你都在胡说什么啊!”我吓得跳了起来,手舞足蹈地辩白着,“哪有这样的事情!”
我只是看过那样的番而已啊!
绝对没有想在现实世界尝试!
“这、这样啊,那好吧,我接受,”她松了一口气,笑了起来,嘴角像是水波的微澜,“那么,似乎无需我每晚替你祈求宽恕。也不用为你降下神罚了。但是…”
“但是?”
“不知道为何…有点遗憾…”